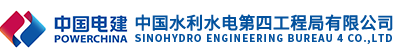愛不會絕跡 |
|
|
|
|
初到龍?zhí)链髩雾椖坎繒r,心間尚存幾分為愛奔赴的滾燙。我辭卻了安穩(wěn)職位,追隨著他的身影,一頭扎入這南渡江畔的水利工地。然而這工地終究是粗糲的,像是河灘上未經(jīng)淘洗的砂礫,磨得人心尖澀痛。鐵皮板房在烈日下蒸騰,四野彌漫著混凝土與江水混合的氣息,夜里蚊蟲如雷,攪擾著思鄉(xiāng)的夢。 我的愛人倒像一株扎根于此的野草,手臂曬得黧黑,眼神里卻只有閘門與圖紙的輪廓。我看著他專注的背影,竟有幾分莫名的陌生,內(nèi)心那點奔襲而來的熱情,在機械的轟鳴里漸次剝落,竟生出了幾絲悔意來。 趁著休假的空當(dāng),我逃也似的回到了家中。外婆切了冰涼的西瓜,弟弟妹妹在一旁嘰嘰喳喳說著對未來的憧憬,而我卻只怔怔地,恍若隔世。外公默默坐在我身邊,目光如炬,竟一眼看穿了我心底那點未干的濕痕。他什么也沒說,只默默戴上他那頂舊草帽,朝我使了個眼色,示意我跟他走。 車子顛簸著,我們最終停在了一處僻靜的水庫旁。石砌的堤壩沉默地橫亙于山谷之間,水面平靜如鏡,倒映著天上云影,幽深得像是藏著無數(shù)歲月。 “這是西營水庫,”外公的聲音沉穩(wěn)而清晰,“當(dāng)年修它,那些娃娃連皮帶骨都撲在上面了。”他的手掌,帶著老年人特有的溫涼,輕輕拍打著身下堅固的壩體,“哪里有什么機器?全憑著肩膀和手,一擔(dān)擔(dān)土石往上壘。渴極了,便趴下去喝渾濁的泥漿水,心里想的是——再難也要讓后輩們喝上干凈水。” 外公粗糙的手撫過壩體上被風(fēng)雨侵蝕的紋路,聲音沉了下去:“當(dāng)年血汗壘成的堤壩,護佑著這一方水土,清清亮亮的水流了多少年,養(yǎng)活了山下多少輩人?你如今在南渡江邊筑壩,不也是把當(dāng)年前輩們流血流汗攢下的恩德,一點一點,還給后面的人么?” 我怔住了。外公渾濁的眼底,竟映出南渡江龍?zhí)翂喂さ氐妮喞且巡皇俏业睦Э嘀且惶幘薮蟮摹⒒钪难}樞紐。那四十多個月晝夜不息的奔忙,那攔截南渡江后形成的浩渺庫容——足足一點四億立方米,那巨大的水脈,正日日夜夜奔涌著,將三億一千萬立方米的生命之源,汩汩地輸向海口,輸向江東新區(qū),潤澤九萬六千畝干渴的田疇。那五百千瓦的電站,也終將點亮無數(shù)燈火。原來,我每日與之搏斗的鋼筋水泥,每一寸艱難,竟都是先輩們恩澤的流轉(zhuǎn)與回響! 回到龍?zhí)翂危隙山囊癸L(fēng)撲面而來,挾著水汽與泥土的腥甜。遠處,巨大的閘門輪廓在星月微光中沉默矗立,仿佛大地深處生長出的骨骼。愛人仍在燈下伏案,電腦上的數(shù)據(jù)仿佛有了生命,牽連著山下無數(shù)人家灶上煮沸的水聲,田里抽穗的微響。我悄然坐在他身旁,靜聽窗外江水奔流,這聲音不再陌生刺耳,而是深沉地拍打著我。 愛,原不是縹緲之物,它早已澆筑在沉甸甸的混凝土里,融入浩蕩清波之中。它從外公那輩人肩挑手扛的血汗里流淌而來,如今又借由我們的手,汩汩不絕地,向更遠的未來涌去。南渡江不舍晝夜,這以水為名的恩澤與深情,亦將如這江水般——永不斷絕。 江聲浩蕩,永恒地流著,我知道那清波之下,是無數(shù)雙手壘砌的沉默堤岸,亦是人世最深沉的愛意——它從歷史深處涌來,又向著更遠的歲月,奔流不息。 |
|
|
|
| 【打印】 【關(guān)閉】 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