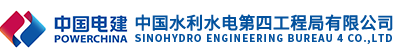在波伏娃的吶喊外,做一個田得梅式的坐標 |
|
|
|
|
晨光漫過項目部辦公室的玻璃窗時,我正對著CAD圖紙研究腳手架的拆卸方案。鼠標在鍵盤上輕敲,發出像春蠶啃食桑葉般的細碎聲響,桌角的綠蘿垂下新抽的嫩芽,葉尖還沾著昨晚空調凝結的水珠。 新來的實習生小陳抱著一摞資料進來,看見我桌角那本打發時間的《第二性》,眼睛亮了亮:“姐,你也看波伏娃啊?她筆下的女性都在為自由吶喊呢。”我指了指屏幕上密密麻麻的數據和注解:“你看這些數據,每一個小數點都在自己的位置上堅守,才能讓渡槽穩穩地架在河面上——這也是一種堅守。” 上月開安全交底會,施工隊的房總拍著桌子說:“這腳手架安裝規范太復雜,現場拼不出來。”我打開筆記本電腦,調出提前模擬好的三維動畫,盤扣的搭接點在屏幕上閃著紅光:“您看這里,我們把原設計的七段搭接改成五段,每段的誤差控制在兩厘米內,現場用激光筆就能精準對齊。”會議室里的反對聲漸漸散了,房總的手指在圖紙上點了點,最后豎了豎大拇指:“還是你們坐辦公室的腦子靈光。” 其實他們不知道,這些“靈光”背后是多少個深夜的演算。有次為了復核腳手架的抗風載系數,我抱著規范手冊在辦公室待到凌晨,窗外遠處的吊車在月光里像個沉默的坐標。電腦藍屏的瞬間,我盯著黑屏里自己模糊的影子笑了——田得梅在天車里手握操縱桿,我在項目部對著藍屏發呆,原來女性的專注,在任何場景里都長得相似。 桌斗里的U盤存著兩年來的安全技術檔案,每個文件名都標注著日期和關鍵詞:“2027.03.15地基沉降觀測”“2025.07.08汛期導流方案修訂”。最底下壓著張黑白打印的照片,是去年去施工現場踏勘時拍的,我站在未成型的調蓄池邊,手里拿著卷尺,褲腳沾著泥點,初入職場的我渴望像田得梅一樣建功立業。 小陳曾問我,整天對著圖紙會不會覺得枯燥。我帶她去資料室翻那些老檔案,2023年的安全日志里,女安全員朱姐用鉛筆標注的水位線依然清晰,旁邊還有行小字:“今日雨大,已組織人員現場值守”。“你看”,我指著那些工整的字跡,“波伏娃說女性要成為自己,而朱姐他們早已在安全日志上寫下了答案。” 下午收到現場發來的照片,腳手架拆卸任務在有條不紊的進行,陽光從網格間漏下來,在地面拼出金色的圖案。我給施工群發消息:“部分腳手架拆卸進度過快,明天調整注意保持平衡。”回復很快跳出來:“收到,劉工把關,我們放心。”夕陽把辦公室的影子拉得很長,我合上電腦時,發現小陳正對著波伏娃的書出神。她筆尖在頁邊寫了句:“原來安全日志里的堅守,遠比書里的吶喊有力量。” 走廊里傳來值班人員的腳步聲,我鎖門前回頭望了眼辦公室,月光正透過紗窗,在圖紙上灑下一片溫柔的銀輝。明天要做的安全月報還在抽屜里,那些等待審批的方案,正像河流一樣,等著我們用專業的技術,引向該去的遠方。 |
|
|
|
| 【打印】 【關閉】 |